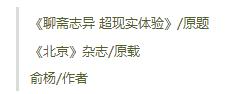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近500篇短篇小说,以严谨巧妙的结构布局、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众多艺术典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文史学家郭沫若评价《聊斋志异》时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著名作家老舍评价《聊斋志异》时也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这部《聊斋志异》如此地别具魅力,难怪著名作家张爱玲要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鬼不仅会说“人话”,还和人谈起了恋爱
涨姿势:弗洛伊德的的心理学解梦,蒲松龄的聊斋学解鬼,还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代,原始的灵魂信仰,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四处游走,灵魂出离肉体或他人灵魂来访时,就产生了梦。当灵魂回归肉体,便是梦醒时分。
《礼记·祭义》记载:“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在整部《聊斋志异》中,写鬼之作约占1/3。小说直接以鬼命名的就有《咬鬼》、《庙鬼》、《谕鬼》、《泥鬼》、《棋鬼》、《饿鬼》、《役鬼》、《黑鬼》、《鬼隶》、《鬼哭》、《鬼津》、《鬼令》、《鬼妻》等。蒲松龄运用这种原始灵魂信仰,给了鬼和人的灵魂以无拘无束的活动空间,为《聊斋志异》构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鬼世界,因而说《聊斋志异》给人“鬼语连篇”的印象并不是空穴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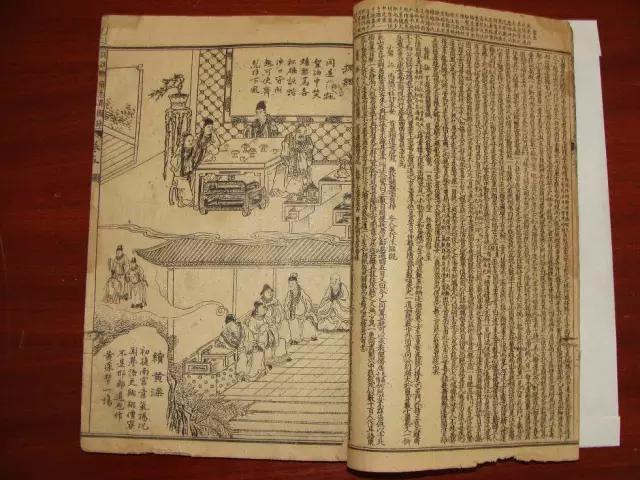
《聊斋志异》中千姿百态的鬼们说出的自然都是鬼话,有趣的是,这些鬼话说起来却跟人一样,他们同样要经历人生百味,体验各式真情。鬼也是需要亲情的,《考城隍》、《耿十八》、《陈锡九》等作品中的鬼都是至孝的典型,他们善事父母、孝感天地,成为社会的典范。
鬼也是重视友情的,《雷曹》中的夏平子、《陆判》中的陆判、《王六郎》中的王六郎,都是对朋友有情有义、赴汤蹈火的典型。鬼更珍视爱情,《公孙九娘》、《鲁公女》、《伍秋月》都是描述鬼魂爱情的佳篇。
古代人还相信,灵魂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四处游走的。当自身的灵魂出离肉体或他人灵魂来访时,就产生了梦。当灵魂回归肉体,便是梦醒时分。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中谈道:“人之梦也,占者谓之魂行。”当“魂行”时,可以遇见不同的人或物,也可以到达不同的地点。《聊斋志异》鬼小说的梦境中,离开肉体的灵魂,甚至可以梦中助人。
鬼于梦中助人在小说里最突出的是《陆判》,梦成为鬼魂助人的主要情境,而且贯穿小说始终。在梦中,陆判为朱生易冥间慧心,使得朱生“自是文思大进,过眼不忘”。陆判又为朱妻易美女之首,帮助朱生获得如花美妻。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借助梦都实现了。

《聊斋志异》全书中谈鬼者达170多篇,在如此多的鬼故事中,又以“人鬼恋”故事最为突出。人鬼逾越了阴阳阻隔,突破了生死界限。人言鬼语幽婉缠绵,想不浪漫都难了。因而一直以来,由《聊斋志异》改编的“人鬼恋”影视剧长演不衰,其中《聂小倩》算得上是影视剧反复翻拍的佳本。1987年,由张国荣、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倩女幽魂》一经上映,就成了经典之作。
聂小倩“十八夭殂,葬寺侧,辄被妖物威胁,历役贱务;腆颜向人,实非所乐”,她被驱使诱惑生人,常以锥刺人足心,或投之以“金”(鬼骨),截取心肝,使人中夜暴亡。她自称“阅人多矣”,然而遇到宁采臣这样“性慷爽自重,生平无二色”的人物,不仅不加害于他,反而对他十分敬重,誓要托以终生,泣曰:“郎君义气干云,必能拨生救苦,倘能囊妾朽骨,归葬安宅,不啻再造。”后来聂小倩与宁采臣配为佳偶。
其实“人鬼恋”故事中国自古有之,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普及,到唐代传奇的继承开拓,再到宋元时期的话本,及至清代“人鬼恋”表现出的脱胎换骨的新貌,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了。
妖气来袭,点赞需谨慎!
涨姿势:蒲松龄笔下的狐女们,不仅长得美还有才,出口成章、谈笑自如,具有和男子一样、甚至超过男子的才气。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对待情感亦无私豁达。这还不够,她们还心地善良,聪明剔透,善解人意,这让我人界女子情何以堪!
《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除了篇数众多的鬼故事外,写狐或涉及到狐的有80多篇,约占总数的1/6。狐捕鼠雀为食,昼伏夜出,性情灵动狡黠,出没于山林地区。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狐妖虽狡诈,却不失娇媚婀娜。蒲松龄是第一位把狐妖人格化的作家,他在《聊斋志异》中赋予狐女新的生命,将她们化身成为痴狂的多情女子,说起妖话来足以颠倒众生。

《聊斋志异》中狐女们很多都姿色出众,以致让男人掉了魂儿。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辛十四娘“振袖倾鬟,亭亭拈带”,莲香“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
《婴宁》篇中,王子服第一次遇见婴宁时,就看见她“捻梅花一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于是王子服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竟然忘记顾及男女之间的忌讳;《胡四姐》篇中,尚生看见胡四姐时,说出了“我视卿如红药碧桃,即竟夜视,不为厌也”;《青凤》篇中,耿生第一次与青凤相见时,更是“神态飞扬,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蒲松龄笔下的众多狐女出口成章、谈笑自如,具有和男子一样、甚至超过男子的才气。《娇娜》篇中的娇娜为孔雪笠割除胸间腐痈时简直是一个手到病除的神医:“乃一手启罗妗,解佩刀,刃薄于纸,把钏握刃,轻轻附根而割,紫雪流溢,沾染床席……口吐红丸,如弹大,着肉上,按令旋转。才一周,觉热火蒸腾;再一周,习习作痒;三周已,遍体清凉,沁入骨髓……生跃起走谢,沉痼若失。”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们,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对待情感亦无私豁达。《小翠》篇中的小翠一出场即是“嫣然展笑,真仙品也”。母亲为报恩把她嫁给无人问津的“绝痴”公子王元丰,她不但没有戚容满面,反而“殊欢笑,不为嫌”。
之后更是“颠妇痴儿,日事欢笑”,一会儿在家中开展“足球运动”,自制小布球,脚穿小皮靴,踢球为乐,让傻丈夫“奔拾之”;一会儿又成了演员兼导演,一出“昭君出塞”唱罢,又来一出“霸王别姬”,“喧笑一室,日以为常”。
在王太常夫妇为小翠出格的游戏将招惹祸殃而惊惶失措、交相诟骂时,小翠的表现是“惟憨笑”、“笑应之”、“俯首微笑”、“但笑不言”、“坦笑不惊”、“含笑而告之曰”,一场仇隙谗毁的大灾也就在小翠的笑中倏然消解了。
狐女心地善良,聪明剔透,善解人意,能够在书生深夜寂寞的时候化做一朵解语花,排遣漫漫长夜的无聊,满足书生精神生活的饥渴;又能在书生贫困潦倒的时候化成一阵及时雨,任劳任怨地帮书生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改变书生贫困的生活。难怪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说:“我读了《聊斋》之后,就很难免地爱上了那些夜半美女。”
人话不说,就成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涨姿势:人话不说不是指人不好好说话,而是有话不好好说。多指巫舞、占卜、符咒等的故弄玄虚,做起法来一张嘴叽叽哇哇的道士们,这口诀自然不是常人能懂的。
人们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在“人话不说”的《聊斋志异》里,草木可以有情,更可以让人悠然神往。《橘树》篇中,陕西刘公担任兴化县令时,有人送他一棵“细裁如指”的小橘树,他不当一回事。但他六七岁的女儿却十分喜欢,“不胜爱悦,置诸闺闼,朝夕护之惟恐伤”。
到了刘县令任满那年,刘公“以橘重赘”不乐意把树带走,刘女却“抱树娇啼”,舍不得离开。从此这棵橘树生长旺盛却从不结果,直到刘女嫁给自己的丈夫庄氏,并且庄氏回到兴化担任县令之后,橘树才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庄氏担任县令三年,橘树硕果累累,第四年却少花少果,刘女说“君任此不久矣”。到了这一年的秋天,庄氏果然卸任兴化县令一职。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曾说:“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理的,也会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聊斋志异》中的这类异物自然是不会说人话的,而在“人话不说”的《聊斋志异》里,一些异人通常也不说人话。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自己幼年到省城赶考时亲眼目睹的经历,写了以杂技魔术为内容的《偷桃》:官员命术人变桃,时值寒冬,哪来的桃子?
术人沉思良久,将一绳索往空中掷出,绳乃悬立空际。又命其子顺绳升天,说是去偷王母娘娘花园里的仙桃。不久果然扔下一个桃子,但是旋即绳被砍断,术人儿子的身体也被肢解,从天上扔下。
术人说儿子是被看管桃园的人发现并被杀死分尸了,于是收拾骸骨入笼,悲泣不已。围观众人皆于心不忍,纷纷解囊以为抚恤,这时术人敲一下笼子,儿子竟钻了出来。

《偷桃》中的术人耍了两个戏法:一是“绳技”,近年来的古装武侠片《剑雨》中,彩戏师的绝技“神仙索”便与其极为相似;二是“起死回生”,术人的“幻术”相当高明。不过,术人嘴里的不管是去偷王母娘娘的仙桃还是儿子被看管桃园的人发现并杀死分尸的说法,显然都是不符合常理的。
当然了,《聊斋志异》中“人话不说”的少不了那些做起法来一张嘴叽叽哇哇的道士们,他们的口诀自然不是常人能懂的,否则人人都能入道了。比如人们都很熟悉的《崂山道士》,其法术非常了得:小小一壶酒便能供所有客人不停地喝;拿纸剪成圆镜,粘贴在墙壁上明如月亮,还能请来嫦娥翩翩起舞;更神奇的是,崂山道士能教王生念着口诀穿越墙壁,令人匪夷所思。
受民间巫风的影响,《聊斋志异》众多小说篇目中,都有巫舞、占卜、符咒等情节。
除了《崂山道士》外,《聊斋志异》中的《赌符》、《宫梦弼》、《雨钱》等篇目都涵盖了道教之术。比如《赌符》中的韩道士会变各种戏法,他画的符咒可以保证嗜赌的人赢钱,并且刚好与自己原来的数目相等;在《宫梦弼》中,宫梦弼埋在砖头下的石子都变成了银子;而《雨钱》中的老翁,竟能让钱像下暴雨一样从梁间落下。
